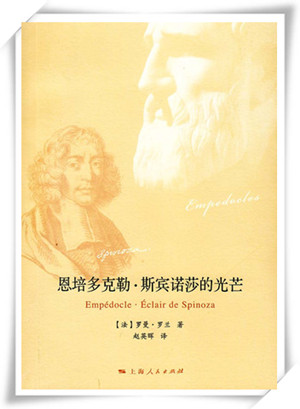斗胆将自己的文字忝列两位诗哲之侧,荣幸之余,委实深感汗颜。恩培多克勒用文字向弟子也向众生传授天地间的真知,帮他们树立新的信仰;罗曼·罗兰用文字为自己也为欧洲召唤指点迷津的神明。而我,深感自己的文字卑微的同时,也想聊尽绵薄,把我听到的真知和召唤尽可能忠实、清晰地传达给更多人;这其实也是恩培多克勒的意思,“好东西,应一说再说”
[1];这其实也是罗曼·罗兰的意思,他赞颂了恩培多克勒由己及彼、自救救人的精神。
罗曼·罗兰创作《恩培多克勒》一文,旨在为当时的欧洲重新寻觅一位哲学导师。曾经师法的古希腊已无力回应新时代的召唤,曾经于19世纪救欧洲精神于水火之间的基督教已无力解决新时代的问题,罗曼·罗兰的思想在往昔的废墟中徘徊游荡,终于在古希腊历史的地平线处,找到了恩培多克勒。恩培多克勒的思想曾照耀过阿格里真托,他的行动曾使阿格里真托摆脱何去何从的昏乱与迷惘;而当时的欧洲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各个民族间矛盾重重,与当年的阿格里真托颇为相像,因此罗曼·罗兰认为,欧洲必然能从恩培多克勒的思想里找到一盏指路明灯,甚至是发现一条康庄大道。
《斯宾诺莎的光芒》为罗曼·罗兰五十八岁时所作,回忆他十六至十八岁间的一次思想转变,促成这次转变的是斯宾诺莎那“火光般的篇章”。那时的罗曼·罗兰正在筹备高等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他对斯宾诺莎的解读,是一个勤勉的学子在黄卷青灯旁的沉思,更是一个胸怀博大的青年在得遇知音时的欣喜。人生中总会有这样的经历:一段乐章或是几句诗行,如同一阵沁人心脾的芳香、一束照彻迷茫的光亮,让你突然间明了自己的期待,并且认定它能将你带进梦寐以求的春天。这就是斯宾诺莎的光芒对于青年罗曼·罗兰的意义,如啜甘酩、如沐春风。从那个幽居在书斋里的忧郁而聪慧的青年,到那个写下这篇文字的享誉世界的文豪,再到那个半生都在为泛人类的梦想奔走呼告的社会活动家,一脉相承的是对和谐与永恒的坚定信仰与不懈追求。有些心绪、有些夙愿、有些情怀,在漫漫征途上初衷不改。于罗曼·罗兰而言,最完满的存在永远是个体生命与宇宙生命的圆融合一,最美妙的音乐永远是全人类在消除了一切隔阂与壁垒之后的壮丽和声。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却都走不出人的思索,尤其走不出古希腊哲人们包罗大千万象的思索。恩培多克勒就是这样一个思索着的人。恩培多克勒并没有完整的作品保留下来,我们只能在普鲁塔克、亚里士多德、拉尔修等古希腊作家的著作中找到他的断句残章。他们或引用恩培多克勒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或者把他的言论当作批评的对象。后世的学者们把这些散落的言论集结起来,就成了今天我们所说的“恩培多克勒残篇”。
《恩培多克勒残篇》,是我在比照两个英译本和两个法译本之后的总结性翻译,力求传达恩培多克勒的原意,英译本之一是William E. Leonard 翻译的The Fragments of Empedocles, (Chicago, 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08);英译本之二是John Burnet翻译的Early Greek Philosophy(London and Edinburgh, A. and C. Black, 1892),这部书影响很大,1919年由法国学者Auguste Reymond翻译成了法语(L'aurore de la philosophie grecque, Paris, Payot & CIX, 1919),这个法译本便是我参考的法译本之一;另一个法译本是Jean-Paul Dumont主编的Les Présocratiques,(Paris, Gallimard, 1988)。当四个版本对同一个句子的翻译差别很大时,我以出版年代距今最近的Dumont 版为准。Dumont版是在参照多位前人编辑的古希腊语版本基础上完成的,当前人意见相左时,Dumont版便根据自己的理解遵从其中的某一个,或者另外给出译法。恩培多克勒的作品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岁月冲刷已然残破,今人所能做的,只是像罗曼·罗兰所说的那样,用想象把它迷蒙的轮廓补全。
遗憾的是,恩培多克勒对文字艺术性的追求,我则无法触及。普鲁塔克指出,恩培多克勒没有极尽词藻之能事的习惯,他通常只是平实地描述。
[2]但罗曼·罗兰却在文章中大量保留了古希腊语原文,并特意提出让读者体会其中的味道,这大概是因为他对于文字形态、音韵美的敏感吧。而且,即便是意义,我也不敢说能够百分之百地传达,柏拉图提出把诗人逐出理想国,因为诗不过是对于摩仿的摩仿,与真理相隔甚远。而这个译本的译本与真理之间岂非隔着万水千山?
恩培多克勒的创作属于“教诲诗(Poésie didactique)”。但John Burnet版并没有按照诗行进行逐行翻译,而是采用了散文体。罗曼·罗兰在《恩培多克勒》一文中也是用散文体翻译恩培多克勒的诗的。Dumont版和Leonard版,是按照古希腊语残篇的诗行逐行翻译的,但并未翻译成诗体,即不讲究格律押韵。我在翻译的时候采用了Dumont版和Leonard版的方法,即尊重诗行,不考虑押韵格律。
罗曼·罗兰精通古希腊语、拉丁语、德语、意大利语,他所阅读的恩培多克勒残篇,包括古希腊原文和意大利语译文,在撰写《恩培多克勒》这篇文章的过程中,他又根据需要把恩培多克勒的部分残篇翻译成了法语。我在翻译《恩培多克勒》一文时尊重了罗曼·罗兰的译本,而未参考其他译本,因而会出现《恩培多克勒》中的残篇与《恩培多克勒残篇》中的残篇在内容上偶有出入,在编号上也偶有出入的情况。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不论是恩培多克勒还是罗曼·罗兰,都怀着这样一种对天下苍生的责任感在为人、为文。而这道义,便是两人终生都在孜孜以求的友爱与和谐,这也是为什么隔着两千三百多年的悠悠岁月,两人的思想会在这部作品里水乳交融。